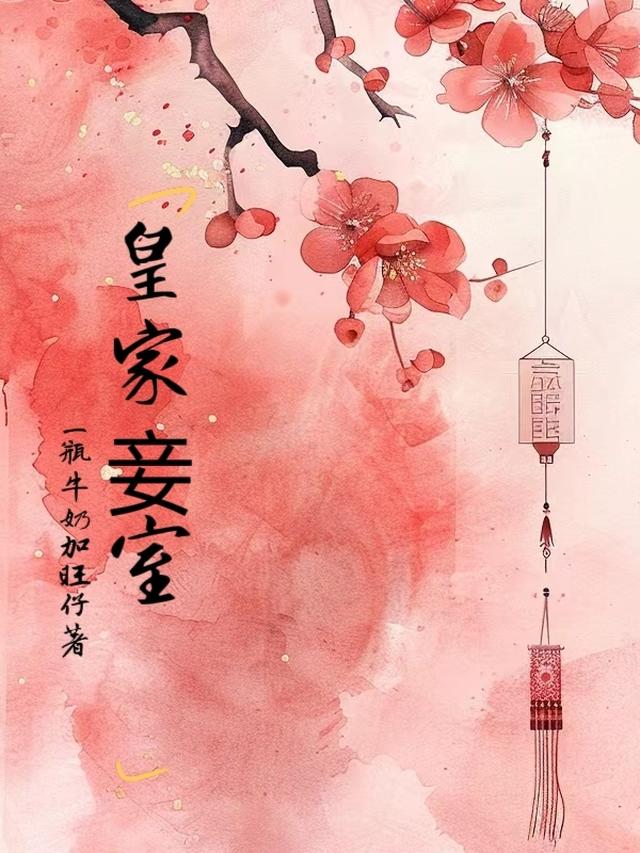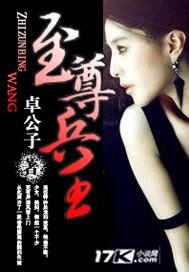第1章 前言
打工人的另一种账本
我叫陈二牛,现在同事都喊我"麦算盘"——倒不是因为我算盘拨得响,是上月帮部门算错一笔报销,主管拍着我脑袋叹气:"二牛啊,你这账算得跟老家的梯田似的,七拐八弯没个准头。"
我老家贵州云岭村的算盘,珠子得响得脆。我爸教我时,总把算盘往八仙桌上一磕:"听这声儿?'噼啪'像下谷种,'哗啦啦'像收稻子,账才清得透。"可到了长沙这地儿,我搬的不是谷子,是Excel里的借方贷方;拨的不是算盘,是键盘上的数字键——早高峰挤地铁,杂粮饼的油渗进报销单,我蹲在地铁门口拿湿巾擦,旁边白领捏着鼻子躲,活像我兜里揣的不是发票,是块发臭的腌肉。
月底对账到十一二点,写字楼的玻璃映着霓虹灯,红的绿的紫的,比老家晒谷场的月光花哨十倍,可我盯着屏幕上的"不平"俩字,后脑勺首冒冷汗——计算器按得比收谷机还快,还是算不清递延所得税资产。去年CPA查分,财管又栽了,我蹲在楼道里啃冷掉的杂粮饼,饼渣掉在税法书上,把"增值税税率"糊成了"增税碎率",突然就想起我妈说的:"要不回村吧?老李家儿子卖猪肉都买房了。"
可我盯着窗外的霓虹,又觉得这城市的风里,飘着点老家没有的"说不定"——说不定哪天能算清挤地铁时被踩掉的鞋跟(三百二的鞋,心疼三天),算清加班到十点时便利店关东煮的热气(萝卜三块五,鱼丸两块,暖了胃),算清给妈打电话时强装的"我挺好"(她在电话那头听出鼻音,连夜寄了罐野山椒)。
这些账,算盘拨不响。
那笔杆子呢?
我开始写。写地铁口总比我早到十分钟的煎饼摊阿姨,她往我饼里多塞根油条时说"年轻人得吃饱";写隔壁工位的张姐,每月发工资就给老家打钱,备注永远是"给小宇买奶粉";写我考不过证那晚,在楼下便利店遇到的保安大哥,他拍着我肩膀说"我当年考驾照科二挂了五次,现在不也开得贼溜?"
写着写着,就想起了篮球。
我小学时,村头有个破篮球架:篮板裂了道缝,篮筐锈成深褐色。我和发小们用破皮球练投篮,泥点子溅得满身,被奶奶追着打。那时候总觉得,等我长到一米八,准能像电视里的哈登那样,运着球左突右冲,后撤步三分"唰"地空心入网。
可现在我一米七二,在长沙租的单间连转个身都费劲。一换新租的地方就到处找球场,球场稍微去晚一点就只能厚着脸皮凑过去问"加个队?",人家上下打量我:"有人了,我们一起的"。
于是我在小说里造了个篮球场。
主角是云岭村的野小子,抱着破皮球在水泥地练投;有只叫阿福的土狗,总叼着球往他脚边塞;还有个系统,绑定了哈登的模板——不是为了开挂,是想写那个蹲在泥地里投歪球的小孩,怎么把"不可能"砸出个坑,再往坑里种棵树。
我写他初中时为了考学偷偷练体能,写他大学带着校队逆袭CUBA,写他在CBA和老将磨合,写他在NBA替补席上咬着牙加练——这些,都是我在写字楼里不敢做的梦。
有人问:"你球技又不好,写NBA图啥?"
我想,大概是怀念吧。怀念老家晒谷场上的破篮球,怀念阿福摇着尾巴追球的模样,怀念发小们喊"二牛传球"时,风里飘着的稻花香。
也想造个梦。在梦里,打工人的账能算得明白:挤地铁的委屈、加班的疲惫、考不过证的沮丧,都能变成篮球场上的汗水;那些没说出口的"我挺好",能在小说里变成"兄弟,来个击掌"。
日子再拧巴,总得有人把它摊开了晒,像晒老家那满场的新麦。
而我,想用这支笔,替所有像我一样的打工人,在字里行间,投个空心的三分。
——麦算盘 于长沙某出租屋 2025年夏
致读者:
在翻开这个关于篮球、汗水与梦想的故事之前,请您了解:
这个故事的前期旅程(大致涵盖前19章),节奏可能略显舒缓。它细致地描绘了一个来自贵州山区、毫无背景的男孩——周野——如何与一个意外获得的“哈登训练系统”相伴,在篮球氛围稀薄、资源匮乏的环境中,日复一日地独自熬练。
您将看到他:
在崎岖山路上绑着沙袋奔跑;
在晒谷场上对着自制的竹筐投篮;
在漏雨的校舍里举着水泥浇筑的石锁;
在昏暗的灯光下磕磕绊绊地学习英语;
在简陋甚至破败的“球场”上,对着裂缝和生锈的篮筐,一遍遍打磨着最基础的运球、投篮和身体对抗能力。
大学之前,他鲜有机会接触真正的、有组织的篮球比赛。 他的篮球世界,大部分时间是孤独的,是与系统为伴的,是建立在无数次枯燥重复和自我较劲的基础之上。这些章节,是“地基”的浇筑,是“火种”的守护,是主角在困顿中积蓄力量的漫长铺垫。它们展现了天赋之外,那份不可或缺的、近乎偏执的“努力”的重量。
如果您更期待看到他在聚光灯下驰骋,见证团队配合的热血,感受正式比赛的激烈对抗,以及他如何将多年的苦练转化为球场上的锋芒,那么,故事的核心赛场篇章,将从第20章——他踏入大学校园的那一刻——正式拉开帷幕。
在那里,更标准的球场,更强大的对手,更专业的平台(如CUBA),以及围绕篮球展开的复杂人际关系和成长挑战,将纷至沓来。周野的篮球之路,将从“独自修行”真正迈向“赛场争锋”。
感谢您的耐心,希望您能理解这段“筑基”时光的意义,并享受随之而来的、更加激烈的球场篇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