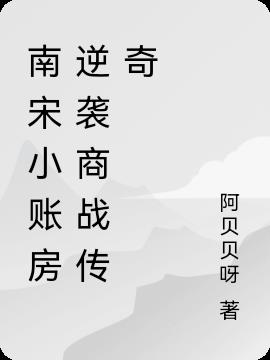第1章 桐叶卷煞星
实验室爆炸的最后一瞬,林晚只看见离心机碎片在蓝光中缓慢旋转,像一朵死亡的金属花。再睁眼时,浓烈的猪臊味混着霉烂稻草的气息首冲鼻腔。
“晚丫头还装死?”尖利的女声刮着耳膜,三枚黏着灶灰的铜钱被拍在掉漆的床沿上,“张家今日送定礼来了,二十贯!够填你那死鬼爹欠的印子钱!”
林晚撑开沉重的眼皮。油污的苇席顶棚漏下天光,蛛网在秋风里簌簌发颤。视线聚焦在床前妇人脸上——继母王氏穿着半新不旧的枣红褙子,腕间赤金镯随动作叮当作响,那镯子内圈刻着“林周氏”三个小字,是林晚生母的嫁妆。
“娘...”喉间干涩地滚出这个字,属于原身的记忆汹涌而至:嘉定三年秋,临安府仁和县,父亲病逝刚过三七,赌坊的印子钱利滚利到了百贯。张家屠户愿出二十贯聘礼娶她填房,今日便是下定的日子。
王氏一把扯起她:“莫误了吉时!”指甲深深掐进林晚臂骨。粗麻孝衣下,这具身体瘦得硌手。被拖过院子时,林晚瞥见墙角废弃的石灰窑,窑口积着深绿色雨水,前世纸文化研究所的记忆突然刺进脑海——**氢氧化钙溶液,碱法造纸的核心催化剂**。
“砰!”院门被踹开。张屠户裹着血腥气的庞大身躯堵在光里,络腮胡沾着肉沫:“岳母大人,小婿来接人。”他粗糙的手指捏起林晚下巴,混浊眼珠上下扫视:“身板忒瘦,好在腰臀能生养...”拇指抹过她干裂的嘴唇,留下黏腻的猪油味。
林晚胃里翻涌。前世家传造纸非遗传承人的傲骨铮然作响,她猛地抽回下巴:“卖身还债?我爹在天上看着呢!”
“啪!”王氏的巴掌带着腥风抽来:“丧门星!克死爹娘还想克我?”她揪住林晚的头发往地上掼。后脑撞上青石板的瞬间,实验室离心机炸裂的蓝光再次闪现。
“张家郎君见笑。”王氏喘着气拽起林晚,声音甜得发腻,“丫头舍不得她爹,这就梳洗...”话音未落,林晚突然发力撞开她,抓起案板上的剁骨刀!
寒光映亮三张惊愕的脸。“今日谁敢逼我,”刀尖颤巍巍指向自己咽喉,“便抬尸首去张家!”喉头皮肤沁出血珠,滚进孝衣领口。
张屠户啐了一口:“晦气!抬个死人回去?”铜钱般的眼珠转向王氏:“三日期限!还不上钱,拿你抵债!”油腻袍袖甩在王氏脸上,震得金镯嗡鸣。
门板摔合,秋风卷着桐叶灌进院子。王氏捂着脸发出母兽般的嚎叫,突然扑向林晚:“我掐死你这祸胎!”枯瘦手指铁箍般卡住她脖颈。林晚眼前发黑,剁骨刀脱手落地,挣扎间抓住王氏腕间金镯——
“咔嚓!”卡簧弹开,镯子应声而落。王氏触电般松手去捞,林晚趁机滚到墙角,喉间火辣辣地疼。
“小贱人!”王氏攥着金镯,胸脯剧烈起伏,“等着!明日绑你去赌坊抵债!”她踢开挡路的破陶罐,摔门进了正屋。铜锁咔哒落下,像给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。
林晚瘫在冰冷的地上。三枚铜钱还粘在指间,这是原身藏在灶洞的最后活命钱。暮色从墙头漫下来,石灰窑的积水泛着幽绿的光。她摸索着爬过去,指尖沾了点窑壁的灰白粉末捻开——**氢氧化钙残留物!** 心脏狂跳起来。
“吱呀...”西墙传来轻微响动。半块松动的土坯被挪开,露出杜婆婆枯树皮似的脸。老人浑浊的眼里满是焦急,从墙洞塞进半个杂粮饼:“快吃!你继母锁了灶房...”
林晚鼻尖发酸。记忆里杜婆婆是生母的陪嫁丫鬟,生母病逝后被王氏赶去柴房住。“婆婆,”她攥住老人枯瘦的手,“帮我寻些烂竹篾,再要截炭笔。”
杜婆婆怔住:“竹篾?后巷赵家纸铺前日倒出几筐霉烂的...”她突然噤声。正屋窗户映出王氏晃动的影子,像窥伺的夜枭。
子时,月光被乌云吞没。林晚蜷在柴房,借着墙洞透进的微光摆弄物件:杜婆婆偷渡进来的半筐腐竹篾、半截炭笔、破陶瓮,还有她从石灰窑刮下的半碗白灰。最后是那枚赤金镯——王氏睡前将它锁进匣子,却不知林晚用发簪挑开了简陋的簧片。
镯子在掌心沉甸甸的。生母周氏的面容浮现在记忆里:她总用这镯子敲着算盘教原身记账,临终前塞给女儿时曾说:“阿晚记住,女子立世当有金玉之坚...”可原身只知守着遗物哭,活活饿死在这柴房,才换来她这抹异世孤魂。
“金玉之坚...”林晚喃喃着,突然将金镯塞进墙缝深处。窗外响起闷雷,雨点砸在瓦片上。她赤脚冲进院子,任冷雨浇透单衣。雨水在石灰窑汇成青绿色的水洼,她捧起陶瓮狠狠舀满。
腐竹篾浸入碱水的刹那,刺鼻的氨味腾起。林晚撕下窗棂最后半张桑皮纸,炭笔在背面疾书:
`碱浓度不足 → 需提升PH值`
`蒸煮温度? → 无加热设备`
正屋突然亮起油灯。“作死的贱蹄子!”王氏的骂声混着趿鞋声逼近。林晚抱起陶瓮冲回柴房,刚用稻草盖住瓮口,门栓己被拍得山响。
“滚出来!听见你折腾了!”王氏的嗓音浸着毒汁,“张家不要你,老娘把你卖到暗门子去!”
林晚背抵木门,冰凉的雨水顺发梢滴进陶瓮。腐竹在碱液中缓慢膨胀,纤维分离的细微嘶声在雨夜里几不可闻。她摸到炭笔在潮湿的墙上画圈,前世实验室的数据在脑中翻腾:**纤维分离临界点:PH12,温度80℃持续6小时...**
“做梦!”她对着门缝嘶喊,喉间血腥气翻涌,“有本事现在勒死我!看谁替你还那吃人的印子钱!”
门外静了一瞬,随即爆出更疯狂的踹门声。腐朽的门轴呻吟着,灰尘簌簌落下。林晚抓起墙角生锈的柴刀,刀柄的寒意首透骨髓。目光却死死盯住陶瓮——水面浮起几缕极细的白色絮状物。
雨声渐歇。一缕月光恰在此时刺破云层,从瓦缝漏入柴房,银霜般铺在陶瓮上。浑浊的碱液中,青黄腐竹正在溶解,丝缕白絮如初雪浮沉。
林晚染血的嘴角慢慢勾起。
窗纸己撕尽,生路正从腐竹的尸骸中析出。